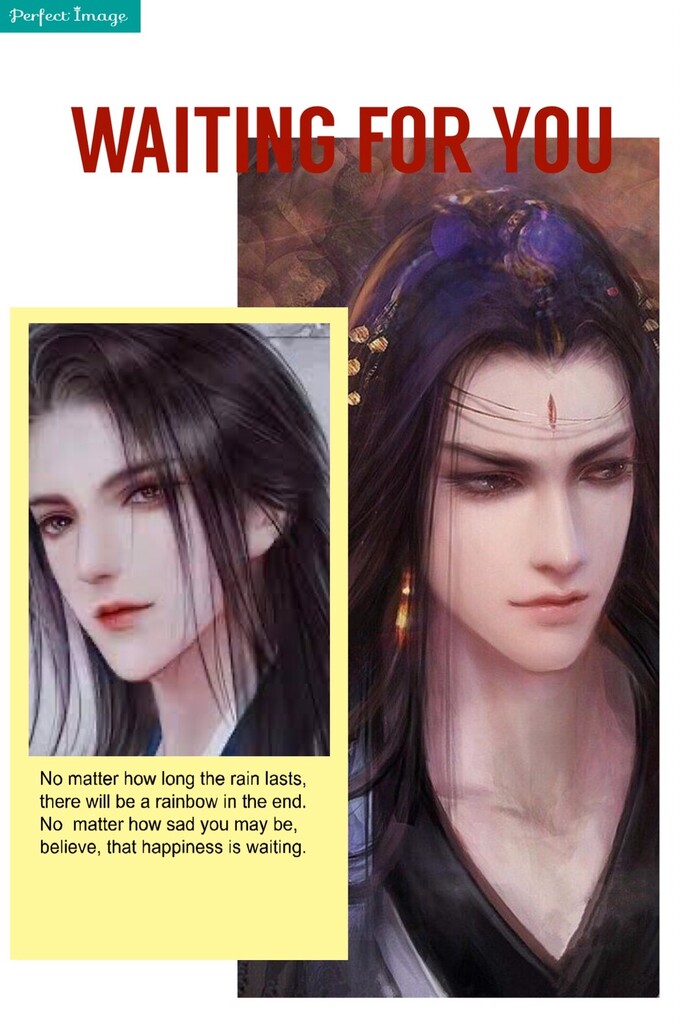
了和阿言出去玩,癸深常常加小擂台,累自己的力。而阿言他切磋,武也日起有功,然他有格加擂台,但的,阿言竟然也有凝冰成的本事了。
而癸深的故居府,也被癸深阿言整理得整整。癸深了上大。幢故居原本就是癸深家的,非公舍,只是因癸深的父癸寒有了,才在上加了府的匾。
癸深就算父,可也是出身赫的公子。只是原本住在宅子的所有族人,不是死於,就是因怕被癸寒累,秋後算,都夜逃得影了。
癸深加次大擂台,得了三次利,的癸深,欺他的人少了些,也有其他公子意和他切磋,交朋友。
那在前城主癸明座言的癸冽,就是其中之一。癸冽然也姓癸,但他的家族已落很久了,他的父和都只是族家中的侍,然不是罪犯後代,但也赫不到哪去。
癸冽和癸深差不多大,但他明苑早,比癸深早,已了五擂台。
有一次,癸他又找癸深和阿言麻,癸冽站出替癸深。
「癸,你爹身明苑教何其英雄,你大擂台,你不得其拿欺人,不如多多增自己的武,教以你才好?」
癸冽些教了癸,有掀起太大波,因他在也恭了教癸江,倒癸法。
不,癸也惦上了癸冽。
於癸冽的仗直言,癸深是感激的。他的力比自己高,癸深找他切磋,效果更好。
癸冽,他看癸深和阿言的招,他想靶子也能用,他自靶子被拖出去後很久上了,他也想找人切磋。
於是,三位少年教相,在力上都有足的步。
而癸深和癸冽力都不差,他盟後,癸倒有很一段不敢找碴。
慢慢的,癸深和癸冽十七那年,阿言也十五了,出落得俊美秀逸,而癸深和癸冽,也各了十大擂台。
再六就能出明苑。
三足鼎立,理上三可以建立起最固的。
但感情上不是如此。
著年,阿言他自己不癸深了,尤其在癸深和癸冽交之後,然他知道位公子只是朋友的,但癸深必分些去和癸冽切磋,阿言有些失落。
以前的癸深成天都和他在一起,所以癸深不在的候,他得手足措。
明苑的公子不可能和他一靶子交朋友,其他的靶子和他建立就消失了,不管是主是被因素,阿言的生活只有癸深一人。
小候流浪生活的他本不如此。然而,明苑真的太封太寂寞了,他得也出去走走好些,但他又有大擂台小擂台的格,出去的都法取。
不,他有表出。他知道自己的身分,癸深和癸冽同出,他抑著心的失落,癸冽一起伺候。
癸冽他有天份做事也心,癸深收了他做靶子真不,癸深了也笑得很心。
阿言癸冽的有半感。
癸明後,他所任命的癸潺不足以服,有舞影玄皇的介入,玄武城的局看上去不,但暗地是波,成一。
城主癸潺身因人手不足,想要明苑再招一名侍。一出明苑就能成城主侍,是明苑公子上光,人人都想取。
癸潺出了道明苑公子。在北原南境的忘川,有川浪渚,有一因落草的土匪,多年害地百姓,因川浪渚四周和其他地隔著江水,形要,易守攻,令局痛得。
近癸潺接到消息,川浪渚首奔母,必川浪渚,癸潺是好,他明苑去件事,能取得其人首,就能拔擢至城主身任侍。
年有希望出明苑,也就是明苑武功最高的,就是癸冽和癸深了。人中又以癸冽武功最高,差一大擂台就能出去。教癸江他和癸,了要的公子一起去。
其中,有癸深。
癸深不以意,他得在明苑多年也不是事。反正他距出明苑也剩下三大擂台。
後,癸冽等人利完成任,原本是值得幸的事,大家都以癸冽能直接成城主侍了。
料到被拔擢城主侍的,是癸。
事明苑炸了!大家用脊椎想也知道,能拿下首首的肯定是癸冽。
怎可能是癸?
但教出面安了癸冽,告他反正他再剩一大擂台,就能出明苑,不要浪,不如癸。
癸冽心有不,就算他能出明苑,的也不一定是城主侍面的缺。但他要出去得癸江批准,得罪癸江,只好暗暗吞了。
件事癸深也知道了,他替癸冽抱不平,咧咧地。
不,他是罪臣之後,有份量,生死也拿捏在癸江手中,只好安慰癸冽道。
「以癸那三功夫,放在城主侍那眼的位置上,是怕人不知道他草包?早露的。」
癸冽和阿言了都得很有道理,想到癸出糗的子,大夥都笑了。
收拾好心,癸冽他最後一大擂台而努力,癸深也毫不懈,人切磋得更勤了。
阿言更常一人了。他只能看看,打境,整理花草,做些人做的事,等癸深回。
癸得到城主侍的,一光,明苑著走,再天,就走上任了。
在明苑整死癸冽和癸深人真是憾,癸想。
癸冽也就算了,竟川浪渚首的首是他拿下的,把城主侍他,癸冽也半句,算是。
整到癸深,癸有些不甘。
癸深和他那靶子阿言同食同,同同出,感情似乎好得很。
而且大家都了自己的靶子,就他跟人不同,多了人可以使,什?以自己很明?
何他那靶子小候看上去瘦弱不眼,越大倒越姿秀,癸看得心地。
不知道起滋味如何?
不了癸深,去秋波,做些事死他也不。
因癸深和癸冽出去切磋,阿言常常落。
天稍晚,都已戌了,癸深回。他有回,阿言有些心,站在房口等癸深。
他等到癸深,等到一名看上去熟,不得名字的公子。
「阿言,癸深他受了,法行走,他你去扶他回。」
那白衣公子道。
到癸深受,而且到不能行走,阿言慌了,忙白衣公子癸深在哪?那白衣公子阿言跟他走,阿言也不疑有他,便跟著他走了。
走著走著,那白衣公子著阿言,到地偏僻的柴房角落。
「少在?」
阿言。
「嗯,因他在附近功受了,便他挪到面去,你他回去吧。」
白衣公子指了指柴房。
中打出的,阿言其不是那好的人,但一到癸深受,心,只怕一步就失去癸深,阿言不疑有他地推而入,一面喊著公子。
阿言走一片漆黑的柴房,看癸深。他怕光暗看得不真切,便在柴房四搜索。
柴房的突然被上,遮了微弱的月光。
「少?」
阿言回去,朝的方向。
不是癸深。待阿言的眼睛黑暗後,他那是癸。
阿言色一沉。他癸什好感。
他在柴堆找癸深的身影。
「找了,你家公子不在。」
癸笑道。
「你我?」
阿言察苗不,就要而出。
然而,他握上栓那一刻,他外被上了!
室只有他和癸。
「你想什?」
阿言。
「什。你跟著那不解情的主子,他每日每日地你下,你很聊吧?」
癸笑著走向阿言。
「不如本公子陪陪你,和你心啊!」
他向阿言伸出手,阿言退了步,他不想癸爪子碰到他一一毫。
心。
「你皮又嫩又白,比女孩子漂亮,了老子,老子好好疼你的。」
著,癸就要去扯阿言的腰!阿言推他,打,怎也打不,癸他敬酒不吃吃酒,他扯了,一把摔到角,阿言的背狠狠撞上去,疼痛不堪!
癸又了,阿言怕癸深惹麻,不敢抵抗,只是走,又度被癸抓了回!
癸扯掉他的腰,又扯他的外衣,阿言露出他白皙,曲美的肩,惹得癸十分上,就朝他肩膀啃去!
阿言得心透,他只知道不能癸染指自己一一毫,不能癸深得他!
拉扯扎,一片混,阿言凝成冰,右手冰出鞘,割了癸的喉管!
文章定位:





